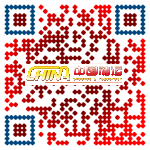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把现代政治的要素归纳为三点:强大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他说,后两个要素是用来制约第一个要素的。现在中国只具备第一个要素而尚未具备另两个要素,因此经济高速增长的现状是难以持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被提升到“长治久安”的高度,说明今后一个较长的阶段内,中国将着力从财政领域出发,补课现代国家的后两个要素,具体说,就是税收、预算和财政体制的法治化,以及建构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完整而严格的责任制。
现代财政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财政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或工具的问题,而是塑造现代国家的利器,有什么样的财政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财政塑造着现代经济、社会文化与价值、有效率的官僚体制、特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塑造着这个国家的人民。
按照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的理解,整个社会是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构成的,而财政是连接这三个子系统的媒介。既然财政是“整个社会”的财政,那么,当财政发生危机时,便会波及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酿成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反之亦然,“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会通过国家的财政危机表现出来。
而我国现实版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把财政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来看待,而是将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财政危机做了颠倒性的理解,使得财政与其中的经济系统的关系显得过于密切,破坏了三大子系统的平衡关系,极易触发整个社会系统出现全局性的危机。新的财政体制改革以衔接三个子系统的节点——财政为主线,对社会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整,其目的,显然不只是处理财政领域的局部问题,而是借此重构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平衡,用以克服已然日益浮现的“整个社会”的危机。
我国改革开放已过35年,但政府职能和公共责任的定位问题仍未解决,一是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趋势难以遏制;二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和事权划分不清晰,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缺乏自主性。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地方政府该做的事,而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做许多中央政府该做的事,地方各级之间也层层向上集权,越到基层越困难。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只占46.7%,支出占比则高达78%以上,比例严重失调。过度集权的结果,是财政秩序紊乱,成为腐败的温床,而效率必然难以成长于其间。
未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其重心应该在地方,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的层面上。今后,建构公共财政体制的逻辑是自下而上,而不再是以往的唯上主义,而且一定是法律而不是一般性的规则起作用。所谓央地“两个积极性”,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实际价值。当前应该做的事情主要是:
——在总体税负不变的前提下重构地方税主体税种,办法是分割增值税和刚刚归并于增值税的营业税,在商品零售环节上征收销售税,此举还对不同地域的公共服务及政府间关系具有难得的公平含义;
——与上文的看法相同,销售税,还有酝酿中的房产税等,其开征与治理的决定权归地方,注意不是中央开恩“放权”,而是法律意义上的“分权”,地方政府也就不必冒道德风险,以不合法的税收优惠“关照”属地企业了;
——在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与经合法授权之后的事权基本适应之后,所谓“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便不再是个如何重要的问题,可以在主体税种共享而不是从税种上彻底分家的基础上建立起规范的分税体制,其实世界上多数分税制的国家就是这么做的;
——建立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最低标准,所谓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才是可能的,接下来,对体制便只是个“分钱”的技术层面的要求了,难度并非大的不得了;
——促进预算和财政信息透明化,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人大审议监督和公众问责,加上民众所交之税与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再被税制割离的因素,体制的纠错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为建构现代财政制度,学者们和政府应该先算一算,未来若干年我国的GDP究竟能供养得起一个多大规模的政府,并开出一份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来,这才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真问题,也是必须回答好的问题。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