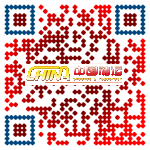老编有曰: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制度具有双重性:对于私权而言,要用“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都是可做的,以发挥大家好的创造力;而对于公权而言,要用“正面清单”约束,凡是没有规定你可以做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不可“创新”地扩大政府的审批与干涉。
法制经济,实际上是确立政府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这在当前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权力与市场关系的模糊,导致权力滥用、市场扭曲、腐败盛行、分配不公,最终将导致市场的失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沦为空话。
明辨正负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分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两种。所谓私人物品,是指那些外部性较小、消费具有排他性、利益边界比较容易界定从而比较容易定价的物品,比如我喝了这瓶水你就不能再喝、我用了这个电脑你就不能再用。这种物品基本上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加以交易,制度也应该鼓励千百万人发挥创新力,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私人物品,在追求更大的私人收益的过程中,提高人们的收入,使人们享受更大的福利。对于提供私人物品的个人与企业,制度应该“敞开口子”让人们去发挥、去竞争、去创新,只有发现创新的产品会有负面的社会外部性时,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时,才对其加以适当的规范与限制,也就是纳入监管的范围。
这就涉及“法治第一原则”,即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凡是原来制度没有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做了是不犯法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发挥创造力,创造出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东西来,经济才能发展。如果个人和企业只能做制度规定可以做的事,原来制定制度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可做了,还谈什么创新?事事都要政府审批了才能做,一定是不会有创新。只有制度允许做的事才是可做的事,一定不是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因此也就一定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
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凡是制度或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就都是可以做的。人们事后可以发现有些新的产品或新的经济活动是有负的外部性的,也就是会对交易双方之外的人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污染了环境或导致金融风险,从而立法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在新的法律生效之前,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并不违法,不应受到惩罚。只有这样,千百万人的创造力才能大大地发挥出来(尽管我们可以从道德上教育或劝说大家应该在创新时就考虑到对别人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另一种产品称为公共产品,其特点是因为其消费的不排他,利益界定比较困难,定价成本太高,导致无法用市场交易的办法加以提供,只能通过某种公共财政的方法由某个公共机构向大众提供。比如一个路灯,你也可以从它下面走过,我也可以从它下面走过,都能获益,但是一旦让我为此付费,我就会说我眼睛好不需要,所以不该付费,出现所谓“搭便车”或“败德”问题。要想搞清楚个人究竟从这个路灯上获得了多少好处、要付多少比例的费用,是件麻烦的事情。所以这时,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办法,就是不做个体的区分,按照同一比例向所有人征税,由一个公共机构来加以提供。国防、外交、消防、环保、食品安全、贫困救济等,都属于这类情况。这就是政府一类的公共机构产生与存在的经济学原理。它们的职责从经济学的逻辑上说就是提供公共物品。
但是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本身具有垄断性,因为不能在一条路上安两排路灯,一个国家不可能需要两套国防体系。这种公共权利的垄断性,导致了一种危险,就是政府权力可能因其垄断性而无限扩张,必须加以约束。如何约束?需要在宪法层面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定。因此,对于政府职权而言,必须是“正面清单”管理:只有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事,才是可做的;法律没有规定可做的事,是不可以随便“创新”的,不可以让权力随意膨胀。
有曰一: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制,就不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只是私有产权保护与定价机制这些基础性的法制,而是还要加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行业监管、宏观调控、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有关公共品的法制,它是所有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相关的各种法制的一个大的集合。在市场化改革初期,人们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较强调与私人品生产与交换相关的市场法制,不太关注与公共品相关的制度。那些对有效经济法制的狭隘理解,显然不符合时代要求。
个人、企业、市场要有约束,政府也要有约束,各有各的职责,这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问题在于,既有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弊端,是把事情搞反了:个人和企业不可以做政府不知道的事,而政府可以任意做其想做的事。
厘清边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定在哪儿,界限问题非常重要,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一定要做好。所以这就有法律的监督在里面,政府要有作为,而不是只是一种应付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所以要通过法制建设来健全。我们要有信心,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信心,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所以四中全会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它鼓励了大家改革的信心,民族振兴的信心,奋发有为的信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更好推动改革?很多问题根据法律法规来推进改革阻力会小很多,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对于农村土地权问题这个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问题农民有意见,比如,按理说产权证、经营证使用权都应该落实到户的,发给农民的,但是很多地方据我了解直到乡里面管起来了,不到农民手里,农民还是不放心,最大的目的是让大家放心这就是不依法,这是一个例子。第二,混合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在推行过程中一直不太顺利,就是因为很多法律法规还没出来,一些条例还没出来,所以国有企业有些顾虑,民营企业也有些顾虑。我加入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把我的财产权交了,他有这种想法。国有体制还是这样,那我不是白搭了吗。这种顾虑也要靠法制建设解除。要解除顾虑,不是靠某个企业人给他作保证解决的,而是要有法为据,第三个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对现在遇到的问题,比如证券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证券老是在上上下下而没有大的情况呢,就是对于证券的法律法规还有些不放心,能不能根据法律来做。比如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能不能做到。
所以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改革是大大的推动,告诉大家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改革。我们过去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认为闯了再说,实际上在改革初期可能有效,现在一定是依法推行改革,所以我认为改革速度取决于法制建设的速度。法制建设了能快一点那改革就快一点,法治监督更严一点大家也就放心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通过法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依法治国对于规范经济秩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华泰证券徐彪认为:首先,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这确实会使得立法博弈难度增加,立法过程更加漫长。修法的过程极其复杂漫长,一个预算法就修了十几年,今年才修改出来,而立法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经常是低于预期的,甚至是遥遥无期的。而提高立法质量,把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使得各种利益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的博弈增加,更是增加了立法的复杂程度和立法所需要的时间。
但是第二,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立法先行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规范政府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法无授权而不可为,等法律出来了,授权你做了,你才能做。这不正是我们新一轮深化户改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吗?让政府收手,政府有法律授权才能做事儿管事儿,这是给市场从根基上松绑,也让政府的行政效率变高。拿税法做个例子,在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中,增值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26%,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几乎涉及了所有行业,但是收取增值税却没有国家法律支撑,依据的是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大家都在关注的房地产税、环保税,以后不是政府说收就能收,有了法才能收,这是防止财税体制改革变味儿从而给市场主体带去束缚。
《人民日报》政文部的微信公共号“人民日报政文”力求通俗易懂地表述法治中国与经济的关系:假如你是一个想开公司的创业青年,也许会感受更深。时间就是金钱,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好的商业创意,如果不迅速付诸实施,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这就要求政府得给力,一个证件办半年,黄花菜都凉了。“法治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知道自己该在哪里收手,然后让市场活力充分涌流。”
有曰二: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立法先行是给市场主体吃定心丸,不用活在过去行政干涉的阴影里。所以立法先行本身就是在推进改革,我们完全可以打消“立法先行导致改革推进速度变慢”的这一担心。
法制经济的贯彻执行,将进一步针对当前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清晰的核心问题,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效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鼓励创新,增强整体经济和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本刊整合)C